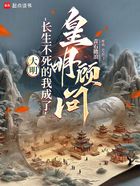
第41章 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于‘起步’
徐良嘴角一勾,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世子言重了,我只是说,燕王可以重新构建一套能够真正推动皇明发展的教育体系。”
“至于程朱理学是否需要推翻,关系不大。”
这句话如同惊雷一般在厅堂中炸响。
朱高炽脸色煞白,手中的茶盏微微颤动。
他虽然听见徐良口中说“关系不大”,但字里行间的意味却令人不寒而栗。
徐良的主张,分明是要从根本上颠覆这座稳固数百年的思想基石!
朱高炽强压住心中的震惊,略显僵硬地说道:“徐先生所言未免太过激进了。程朱理学自南宋以来便为朝廷立国之学,是维系天理人伦的根本。若动摇此根基,恐怕……”
他没有说完,眼神中已流露出强烈的不安与抗拒。
“阿弥陀佛。”
坐在一旁的姚广孝轻轻念了一声佛号,双手合十,闭目片刻,似在平息内心的波澜。
他随即睁开眼,神色复杂地看向徐良:“程朱理学乃道统之源,是士林尊奉的圭臬。若要动它,恐怕天下士林皆不答应。”
姚广孝这话虽是劝阻,但分量极重。
他一生历经风云,对于士林的势力再清楚不过,轻易撼动道统,无异于与整个知识阶层为敌。
徐良并未回避,反而坦然点头,语气坚定:“程朱理学的核心是‘存天理,灭人欲’,看似教人向善,实则是一套钳制思想的工具。”
“它用繁琐的道德教条束缚人性,将朝堂变成了空谈圣贤之理的场所,而非治国安民之地。”
他的目光缓缓扫过两人,语气越发犀利:“对于士人,它是一道看不见的枷锁;对于百姓,它是阻碍发展的藩篱。”
“单以这样的学说取士,只会让皇明管理系统逐步僵化。”
这番话一出口,厅中空气仿佛凝滞了片刻。
朱高炽抿着嘴唇,他心中隐约觉得徐良的言论不无道理,但又觉得这番激进的想法太过冒险。
他终于开口,语气有些发紧:“徐先生,程朱理学纵使有其不足,但它提倡的‘天理人伦’,不正是维系朝廷和百姓的根本吗?”
“若贸然推翻,岂非天下大乱?”
“大乱?”徐良冷哼一声,“真正造成天下大乱的,是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官僚。”
“他们借助这套道学的外衣掩饰贪婪与无能,让百姓忍受饥寒交迫。这样的‘道理’,究竟是为了谁?”
姚广孝微微蹙眉,睁开眼睛直视徐良,声音有些颤抖:“徐先生,您的观点的确有冲击力,但老衲不得不问,若非程朱理学,您所谓的‘新教育体系’又是什么?”
徐良微微一笑,转身踱步回到桌边。
他端起茶盏抿了一口,神色从容:“所谓新教育体系,是抛弃那些不切实际的空谈,把目光放到实事和百姓的实际需求上。”
“百姓需要的,不是天理人伦的教条,而是能够吃饱穿暖、安居乐业的政策。皇明需要的,不是一个个死读书的酸儒,而是有真才实学、能办实事的人才。”
他说到这里,语气逐渐高昂:“只有从根本上改革思想教育,提倡实学,才能让国家真正强盛。”
朱高炽听得心情愈发沉重,双手无意识地紧握成拳,目光在徐良与姚广孝之间游移。
他的内心翻涌着矛盾——既认同徐良的一些观点,又深感其言论的危险性。
徐良见状,话锋一转:“北宋之时,有一位名叫沈括的官员,他通晓天文、地理、医药、数学,甚至军器铸造,堪称博学之士。”
“他撰写的《梦溪笔谈》,不仅记录了许多创新的实用技术,更对后世科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朱高炽听到“沈括”二字,眼中掠过一抹讶异,轻声自语:“沈括……《梦溪笔谈》……”
他记得曾在书房里翻阅过这本书,但当时因为内容艰涩而匆匆放下。
如今听徐良提起,他竟感到一丝惭愧,像是错过了某种深远的智慧。
正在此时,门外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威严的声音响起:“本王倒要听听,什么样的人才配得上你徐良口中的‘实学之才’。”
朱高炽与姚广孝心头一震,纷纷起身行礼:“燕王殿下。”
朱棣身着玄色蟒袍缓步走入,神色冷峻中带着些许疲惫,他显然刚从军务中抽身而来,但眼中的精芒依旧锐利如刀。
朱棣目光落在徐良身上:“徐疯子,你刚才所言,本王在门外已略听一二。”
“沈括确实是大才,但他不过是北宋的一介官员,与如今皇明的局势,真能扯上关系?”
徐良冷哼一声,显然还在记挂朱棣假扮身份骗他的事。
他坦然答道:“沈括的意义,不在于他的个人,而在于他所代表的‘实学’之道。皇明缺少的,正是这样的人才。”
朱高炽与姚广孝不禁为他的无礼,抹了一把冷汗。
朱棣冷哼一声,语气带着嘲讽:“如今的朝堂里,尽是无用之人?”
徐良毫不避讳,直言道:“不少官员受科举制度影响,只知空谈仁义道德,却未曾真正踏足民间。”
“若黄河决堤、残元入侵,仅凭他们的四书五经,恐怕百姓早已尸横遍野。”
朱高炽听得心头一颤,面色隐隐发白,犹豫片刻后低声劝道:“父王,话虽如此,但程朱理学毕竟是国本,自南宋以来,士林皆以此为尊,视为立身之根基。”
他停了停,神色越发凝重:“若是动摇这根基,恐怕天下士林之怒难以平息,反而会为靖难大业增添阻力。”
朱棣目光如电般扫过朱高炽:“你觉得徐良的提议不可行?齐泰、黄子澄这些人便是程朱理学的高徒!”
朱高炽感受到那凌厉的目光,喉结轻轻滚动,却难以开口反驳。
他的视线不自觉地投向徐良,显然希望从这位狂士口中得到些支持。
然而,徐良依旧一副淡然模样,似乎全然未被气氛影响。
他微微一笑,目光转向朱棣:“程朱理学扎根已深,短时间内确实不宜彻底硬撼。”
“但天下士子,不应只背诵圣贤之书,而应学会将学问化为实践之器。”
朱棣的声音带着丝冷意,显然对这类理论之谈不太感冒:“如何实践?若只是空谈‘实学’,不过是换了个说辞罢了。”
“本王要的,是能解决问题的法子,而不是一套新的学派名号。”
徐良神色难得认真:“所谓实践,便是教人以有用之学,以北平为基地,设立一所新式书院,教授真正能造福民生、强盛国力的学问。”
他略微顿了顿,目光灼灼地望着朱棣:“诸如农业改良、水利工程、军器设计、律法实务,甚至海外贸易。”
“这样的士子,不必人人成为沈括,却至少能各司其职,为皇明分忧。”
朱棣闻言,眼中闪过一丝若有所思的光芒。
然而,他很快收敛思绪,脸上重新浮现出冷峻的神色:“此法听来虽好,但书院设立、士子成才,非一朝一夕之事。”
“而今靖难大业正值关键,哪有余力容得这些书生慢慢成才?”
徐良闻言不卑不亢,缓缓说道:“时间的确紧迫,但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于‘起步’,而非立刻求全。”
“若你能下定决心从现在开始推动,虽无法立刻见效,但长远来看,朝堂的文风必然会逐渐改变。”
他语气一顿,仿佛要将自己的信念深植在朱棣心中:“更重要的是,当新的官僚集团崭露头角时,殿下便可借此力量迁都北平,进而对抗江南士子集团的掣肘。”
“到那时,朝堂之局也将因此而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