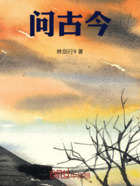
第7章 《青玉案》背后的孤寂:辛弃疾的职场之路
淳熙七年(180年),四十一岁的辛弃疾,再次任知隆头(今江西南昌)府江西安抚史,拟在上饶建园林式的庄园,安置家人定居.这一刻,安置家人定居,已为下半生做准备的辛弃疾,似已接受自己的命运:
在江西了却残生,与自己无限期望却又无限的离他远去的理想做最后的道别,那位敢为理想带队冲万人敌营的猛男,也已垂重老矣。
《青玉案元夕》是辛弃疾入职南宋官场不久后所写,写的是繁华背后的孤寂落寞,最后一句,最为动人心,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一个职场新人精神离职宣言:我司雇我在,人在心不在,我还要寻找心中的那个“他“。
来时意气风发,晚年锐气尽丧,只剩一点报国之心在日渐消磨,身躯日渐老去,壮志逐日消亡,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在表示:他已放弃过去,彻底从一个一心恢复中原的武将,转化成接受现实的文人。
清淳八年(118)春,开工新建带湖新居和庄园,辛弃疾根据地势走向亲自设计高处建舍,低处辞田的庄园格局,看着自己一手设计出的巧夺天工的庄园,一股豪情从心底深处急速升起,并对家人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他又将带湖庄园联名“稼轩。
自此,此后的他以稼轩居土自居,也就是在这时,经济理想与仕途的双重打击,看清自己大起大落落落落的本质,辛弃疾才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无为众人所容。(《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归隐的准备。
可说到底,“刚拙自信“,不过是辛弃疾给自己最后的颜面!自信,是错吗?决不是。自信,是对自己实力的肯定,对自己的认可.这恰恰是一个人最需要的品质,可宋朝需要吗?当时的社会需要吗?
窗外的狗叫了,其他的狗也跟着叫,但它们不知道为什么叫。生活咸淡,他写:鹏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举目无亲,心情暗淡又写: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这样才华横溢的他,自然清楚自己的现状,明白自己一个坚定的抗金主义者,是无法在一群投降主义者中生存不下去的,存在都不可能,只是自己不愿妥协罢了。
就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同年十一月,由于受到弹劾,官职被罢,带湖新居正好落成,辛弃疾也借机回到上饶,幸远地开始他中年以后的闲居生活,此后的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状和抚建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闲居。虽说解开官职的缚束,赋闲在家,可辛大爷却是个闲不下来的主在审湖新居即将建成时,他写《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
用以表达自己久经官场黑暗,故而对隐居生活的向往,隐居时,写《清平东一村居》,这首诗描绘了一个农村家庭的生活日常,词中的“筝檐低小,溪上青青草“和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穿翁媪!生动和谐的勾勒出一幅和谐的农村生活图景体现出辛弃疾对简单生活的向往。
他的诗词风格豪迈,大气,可他毕生的梦想就是驱除革达虏,恢复中原,因此,他最开始的定位是武将,这一点,他没有忘!因此,辛弃疾建立一支以一千人为额的飞虎军,专门负责湖南地区的防御工作,在得到朝延批准后,他开始着手组建飞虎军、期间虽遇到资金短缺,人员招募,装备采购等问题.但这可是凭一己之力拉起2000人马的辛弃疾,这些于他而言不过覆手间,就可解决。在组建时,辛弃疾来了波废物利用,动员囚犯参与建设,并用税收来弥补军费开支。
飞虎军一建成就平定湖南地区的叛乱和盗贼、有效的维护当地的治安和稳定,使湖南地区安宁工很长一段时间,后全军下举入侵,飞虎军在多次与金人交战中表现出色成为南宋最为精锐的一支队伍,金人称之为“虎儿军“。闻风丧胆,虽然由于南宋朝廷的内部矛盾和女人间的倾轧,辛弃疾最终未能在仕途上取得更大成就,但他留下的飞虎军却成为南牢抵抗外敌的重要力量。
淳熙十五年(188年)冬,好友陈亮从浙江永康专门来拜访辛弃疾,老友多年未见,聊到兴起时,就否不住互诉衷肠,于是两人前往铅山,用长歌一问一答的方式倾诉多年遭遇,这次遭遇称第二次鹅湖之会(即辛陈之晤)。
鹅湖之会之后,辛弃疾又两次出山做官。两次出山,无果而归,虽已闲居,报国之心从未熄灭.两度出山只为完成自己的终生目标:恢复中原。
惜!六年奋斗,殚精竭虑,只为再起北伐之军,洗靖康耻,回故土,夺燕云!却一朝尽废,叹,知天命的年龄,只想为自己毕生的梦想再努力一把。却不曾想是镜中花,水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