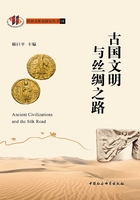
第一节 远东希腊人王国与丝绸之路
远东希腊人王国是指从公元前3世纪中期以后,存在于中亚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和印度西北部的印度—希腊人诸王国。这些希腊人虽然孤悬远东,却仍然努力坚持自身的希腊文化传统,试图维系自身与东部希腊化世界的经济文化联系,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得不接受当地文化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一个以希腊文化为主导,同时融合波斯、印度和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文化因素的多元文明——远东希腊化文明逐渐出现,一条维系地中海世界和远东希腊人王国的经济和文化通道逐渐形成[1]。张骞就是在这样的时刻,风尘仆仆地来到了中亚,从而宣告了这条东西方千年交流之路的开通。从这个意义上说,亚历山大东征与张骞通西域,对于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发挥了同样重要的历史作用。
一 亚历山大在远东的征服与塞琉古王国的东扩
(一)亚历山大之前希腊人对远东地区的朦胧认知
本文的远东地区特指中亚和印度,以区别于一般的东方或伊朗高原及其以东的所谓“上省”地区。由于中亚、印度是波斯帝国最东面的扩张之地,也是后来中国文明与希腊化文明的最先接触之地,以帕米尔为界的丝绸之路东西线连接之处。因此,简单回顾一下亚历山大之前希腊人对此地的了解对于探讨远东希腊人王国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是必要的。
在所有的西方古典作家中,最早提及中亚和印度地区的是希腊探险家斯库拉克斯(Scylax),他曾在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Darius I)的派遣下,率领船队考察印度河口及印度洋沿岸的部分地区。[2]在其记载中就有来自印度的名为κυνáρα(具体不详)的物产和某一名为τρωγλοδúται的民族。[3]另一位较早提到过印度地区的学者是米利都(Miletus)的赫卡泰欧斯(Hecateus)。他在《大地环游记》(Perigesis)中,对斯库拉克斯的记载进行了考证,不仅肯定其笔下的“κυνáρα”的确产自印度,还另外提到来自印度的犍陀罗人(“Γανδáραι”)。[4]虽然,这些早期的零散记载语焉不详,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是希腊与印度早期交往的重要证据。
希腊人有关中亚和印度的第一份详细记录出自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历史》(The Histores)一书中,他以斯库拉克斯和赫卡泰欧斯的记录为基础,详细梳理了前者的航线以及印度河地区的大致情况;[5]同时,他还依据普洛孔涅苏斯岛人阿里斯铁阿斯(Aristeas of Proconnesus)的远东之游,对斯基泰人(Scythians)、伊塞顿人(Issedones)等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和居住地概况做了介绍。[6]虽然,对于希罗多德记载的真实性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但从考古发现上看,无论是苏美尔铭文上提到的来自印度的货物,还是出土于阿曼(Oman)沿海的印度圆柱形印章,或是出土于阿拉木图(Almaty)附近的斯基泰金人,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早期地中海地区与中亚、印度以及北方游牧部落间存在着一定的交往。[7]
在希腊人大规模东进之前,波斯人是东西方经贸和文化往来的主导者。公元前550年前后,波斯帝国崛起于伊朗高原。数十年间,小亚(Asia Minor)、两河流域(Mesopotamia)、埃及(Egypt)、中亚、印度西北部,甚至欧洲一部分也都纳入了它的版图。小亚的希腊人城邦与帝国东端的巴克特里亚和犍陀罗地区,都处于同一个帝国之下,双方的联系和了解进一步加深。
为了加强对庞大帝国的控制,阿黑门尼王朝在境内开辟了两条大道,一条是从王都之一的苏萨(Susa)到小亚以弗所(Ephesus),史称“御道”(Royal Road)[8];另一条经伊朗(Iran)高原,直通巴克特里亚(Bac-tria)和印度西北部地区。[9]这两条道路沟通了从地中海到印度河之间的联系。原产于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Sogdiana)的天青石(Lapis la-zuli)能够出现在近东地区;[10]远征希腊的波斯军队中能够出现来自印度的士兵,或许都与这条路有关。[11]这些道路未来将构成丝绸之路西段的主要干线。
希腊人也逐渐被印度人知晓。波斯语中,希腊人被称为“Yauna”,梵语(Sanskrit)、巴利语(Pali)中表示希腊人的“Yavanas”、“Yona”等词语,很可能就是由此转写而来。[12]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赛里斯”(Seres)一词上。这个词汇最早出现于公元前5—前4世纪的希腊医生兼史家克泰夏斯(Ctesias)的著述中。虽然这一名称的具体所指,目前学界仍有争论,但包括斯特拉波、普林尼(Pliny)、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在内的古典作家们都将其指向于一个遥远东方的产丝之国。[13]
此外,一些希腊人也开始长期定居中亚。希罗多德就曾提到,波斯帝国在征服北非巴尔卡(Barca)的希腊殖民地之后,将当地的希腊人送到巴克特里亚。[14]此外,还有一些希腊人自愿移入。比如斯特拉波(Strabo)提到的布兰开德族人(The Branchidae)。他们的家族本是米利都城邦狄德玛(Didyma)圣域阿波罗神庙的祭司,负责神庙的安全,但在希波战争中,他们背叛同胞,将神庙的财宝献给了波斯。波斯人战败后,他们害怕受到报复,请求薛西斯(Xerxes)将他们带走,最后定居在了索格底亚那地区。[15]
因此,当亚历山大进入中亚、印度之时,展现在他眼前的并非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也非一片蛮荒之地[16],而是波斯帝国长期统治和经营的边地行省或是刚刚独立的地方王国,它们都具有鲜明的民族和文化特征。
(二)亚历山大在中亚和印度的征战
亚历山大在中亚、印度的征服对未来丝绸之路在此地的的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于沿线新城市的建立。
公元前330年秋,为追击挟持大流士三世逃跑的贝苏斯(Bessus)和应对阿里亚地区(Ariana)的叛乱,亚历山大不得不改变直接进攻巴克特里亚的计划,南下阿里亚、阿拉科西亚,再北上越过兴都库什山,从东北方向进入巴克特里亚。为了保障后方安全和后勤补给,亚历山大在此次行军的途中,修建了一系列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城市,其中,比较著名的是马尔基亚纳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inMargiana)、阿里亚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in Ariana)、阿拉科西亚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in Arachosia)以及高加索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of theGaucasus)。[17]此外,在进军阿姆河、锡尔河和印度河流域期间,亚历山大同样派人修建了阿姆河畔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Oxiana)、最远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Eschate)、印度河畔的尼卡亚(Nikea)、纪念其战马的布西发拉(Bucephala)等城市。[18]
虽然,亚历山大的建城活动起初是出于军事的考虑,甚至还有安置伤残老兵的意图,但是,伴随着这些城市或驻防地的建立,中亚和印度西北部的商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完善。
一方面,从里海沿岸到印度河流域的路线增多了。商旅们既可以选择从赫卡尼亚(Hyrcania)出发,先到马尔基亚纳的亚历山大里亚进行休整,然后直接东行巴克特里亚,翻越兴都库什山进入印度;也可以选择南下,绕行阿里亚的亚历山大里亚和阿拉科西亚的亚历山大里亚,然后再沿赫尔曼德河(Helmand)向东经波伦山口(Bolan Pass),或向东北经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进入印度。从后世的历史来看,这条路线后来也成了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支线之一。《汉书·西域传》的有关记载对此路线有所反映:“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可能就是Alexandria in Arachosia,阿拉科西亚的亚历山大里亚——笔者注),南道极矣。转北而东得安息”。[19]
另一方面,希腊式城市在索格底亚那、费尔干纳(Ferghana)谷地和印度河流域的出现,为商路向这些地区的开辟提供了可能。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索格底亚那和费尔干纳地区的商贸实际上是由当地的游牧民族所主导,并不存在明确的贸易路线。波斯帝国在当地也只是建立一些据点,如远在锡尔河畔的居鲁波利斯(Cyropolis,居鲁士城)等[20]。至于对印度的认识,希腊人还比较模糊。亚历山大在征讨印度时,对希腊神赫拉克勒斯(Heracles)、狄奥尼苏斯(Dionysus)在此地的活动传说尤感兴趣,意欲超越他们走得更远。[21]得益于这些城市的建立,后来塞琉古王国和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希腊人在此地有了立足之地。后来的张骞在中亚的行程是经大宛和康居(索格底亚那),到达大月氏、大夏(巴克特里亚)。[22]这条路线与前面提到的经阿里亚和阿拉科西亚,然后再到巴克特里亚的绕行线以及经木鹿绿洲直接到巴克特里亚的直行线一起,构成了后来丝绸之路在中亚和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基本走向,亚历山大所建立的这一系列城市大部分后来也成为了这些地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亚历山大东征也同时推动了希腊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亚历山大对于他所降服的东方民族态度是宽容和友好的。除任用当地人为总督外,还鼓励他的将士与当地人联姻。他在中亚时与巴克特里亚一位贵族的女子罗克珊娜(Roxana)结婚,目的就是通过联姻笼络当地的统治者,使他们倾心归顺。
此外,他还招募当地的波斯青年人接收马其顿式的军事教育,后来还把他们编入了伙友骑兵,据说总数有3万人之多。[23]虽然,亚历山大的这种东方化倾向激起了马其顿人的强烈不满,但从客观上看,这些做法一方面有助于拉近希腊人和当地人的距离;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有助于希腊文化在中亚和印度等地区的传播。
公元前323年6月,亚历山大病逝于巴比伦,其帝国很快分崩离析。然而,亚历山大在中亚和印度的遗产仍然继续发挥着作用。他的东征路线,大致上就是后来丝绸之路的主要干线;他在征战途中建立的城市,有的成了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他在此地的统治被他的继业者继承延续,他所带来的希腊文化,通过塞琉古王国、巴克特里亚、印度的希腊人王国,在中亚、印度长期流传,成为此地多元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塞琉古王国时期的中亚和印度
亚历山大去世后,他的帝国很快被部将瓜分完毕。塞琉古一世(Seleucus I)几乎继承了亚历山大在亚洲的全部遗产。公元前305年前后,他开始向巴克特里亚和印度进军。然而,塞琉古收复印度的计划最终未能如愿。他遇到了新兴的孔雀帝国(Maurya Empire)的强烈抵抗,他不得不和旃陀罗笈多(Candragupta)议和,以获得500头战象和双方联姻为条件,放弃了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大部分地区。
虽然,塞琉古收复印度的行动以失败而告终,但塞琉古王国积极修建城市,组织殖民,东西方的交往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
这一时期沟通中亚和印度的商路主要有北线、中线和南线三条,其中,北线证据相对较少,英国学者塔恩(W.W.Tarn)甚至认为其不存在。[24]不过,这一说法显然有误,因为斯特拉波就曾提到,阿姆河航运比较便利,来自印度的商品可以沿河而下运送到赫卡尼亚并转运黑海地区。[25]中线主要由两条陆路和一条海路组成。其中,海路以斯库拉克斯探索印度河的航线为基础,从印度河到波斯湾,然后经底格里斯河(Tigris)到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城(Seleucia on the Tigris),最后至东地中海各地。陆路主要以波斯的道路体系和亚历山大的东征路线为基础,一条从印度出发,经高加索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后来的Kapisa,中国史书中的迦毕试),先到阿富汗的巴克特拉(Bactra),然后由此向西到到达木鹿(Merv),然后经赫卡通皮洛斯(Hecatompylos,又名百门城)和埃克巴塔纳(Ecbatana),最后到达塞琉西亚。另一条路线从印度出发,绕道喀布尔(Kabul)、加兹尼(Ghazni)和坎大哈(Kandahar),接着再折北经赫拉特(Herat)到赫卡通皮洛斯,最后抵达塞琉西亚,最后至东地中海地区。或者从坎大哈西行,经卡尔马尼亚(Carmania)到波斯湾。这条路要经过沙漠地带,难以通行。除此之外,一条新的海上航线也在这一时期逐渐被人们所使用,其主要的走向也是印度河到阿拉伯海一线,但直接去往阿拉伯半岛南部,然后从纳巴泰(Nabatae)上岸,所运货物经纳巴泰人(Nabateans)或者阿拉伯人转手之后,到达大马士革(Damascus)或者是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in Egypt)。[26]
为了巩固对中亚的控制,塞琉古王国对该地的部分希腊城市进行了重建。例如:马尔基亚纳的亚历山大里亚。按照普林尼和斯特拉波的记载,该城后来因周边游牧民族的侵扰而被毁,安条克一世(Antiochus I)将之重建,并更名为“马尔基亚纳的安条克城”(Antioch inMargiana)。[27]同样得到重建的城市还有所谓“最远的亚历山大里亚”,该城也曾一度因游牧民族的侵扰而被毁,后来也得到了重建,并更名为“斯基泰的安条克城”(Antioch in Scythia)。[28]虽然,相对于叙利亚和两河流域而言,塞琉古王国在中亚建立的城市相对较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零星的城市如同茫茫大海中的岛屿,分布于塞琉古王国治下广阔的中亚地区,为各地的交往提供了便利。
在众多城市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阿伊·哈努姆遗址。该城位于阿姆河与科克查河(Kokcha)交界的河口上,是中亚地区遗址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希腊古城。部分学者认为其很可能就是亚历山大所建的“阿姆河畔的亚历山大里亚”。[29]从布局上看,该城比传统的希腊城市更注重城市防御,四周有厚实的城墙和防御用的堡垒。城市内部以小山丘为界分为两个大区。山上的大区由卫城和一座露天神庙所组成,属于宗教与公共活动区;河畔区则主要是宫殿群、剧场、体育馆、主神庙、祭所、军械库等公共建筑以及大量的私人住宅。同时,该遗址中到处可见希腊柱廊式建筑遗迹以及科林斯式(为主)、爱奥尼亚式、多利亚式三种风格的柱头。浴室地板则铺设有由海豚、海马和海怪等海洋动物构成的马赛克图案,石砌喷泉的出口用希腊喜剧人物的面具进行装饰。[30]这样的选址、布局和装饰显然是对希腊本土城市的模仿,但当地的因素也很明显。
在这座城市中,希腊化特征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希腊式的体育馆和剧场。阿伊·哈努姆的体育馆与传统的希腊体育馆类似,主体是一座庭院,由四周的房屋和柱廊围绕而成。阿伊·哈努姆的剧场建在卫城的内坡上,整体呈半圆形,比著名的埃庇道鲁斯剧场(Epidaurus)略小,半径为42米,高17米,一次性可容纳5000人之多。按照希腊的传统,体育馆和剧场是希腊人日常公共活动的中心。阿伊·哈努姆遗址的体育馆和剧场能有如此庞大的规模,证明该城希腊人口众多,希腊化文化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此外,希腊语的使用也是希腊化文化的重要体现。在建城者基涅阿斯(Kineas)的英雄祠(Heroon)中有一块石刻铭文,上面是来自希腊德尔斐神庙的格言,相传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克利尔克斯(Clearchos)于公元前275年前后拜访此地时留下的。[31]
虽然,希腊人一直在尽力保持他们的希腊化文化生态,但从他们踏入这片土地伊始,他们就不得不面临周围东方文化的缓慢影响,这种影响在阿伊·哈努姆遗址的宫殿建筑上体现得最为明显。由于移居此地的大部分希腊人并没有建造王宫的经验,这就使得建筑师们只能采用波斯式或者巴比伦式的宫殿为蓝本,辅以希腊艺术风格的装饰。从结构上看,阿伊·哈努姆的宫殿主要分为办公区、居住区、库房三大部分。王宫正门是一座大庭院,四周是科林斯式柱廊。南面柱廊后是门厅,由18根科林斯式石柱所组成纵向列成三排。按照发掘主持人伯尔纳(Paul Bernard)的解释,这种布局很可能是对波斯式宫殿的模仿。[32]
除宫殿以外,神庙的建筑风格同样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从结构上看,阿伊·哈努姆的神庙与传统希腊式的柱廊结构神庙有很大的不同。它们有较高的石基,整体呈一个“凹”字型,有露天的前厅和祭祀场所,结构更类似于两河流域或者波斯帝国的神庙。以位于皇宫不远的主干道的一座神庙为例,它建于有三个台阶的基面上,祭祀场所位于宽大的前厅之后,神像正对门口,两旁还有圣物室。[33]卫城西南角的另一处神庙则是一个露天的台阶型平台。按照伯尔纳的观点,这种建筑设计很可能来自于波斯,因为波斯人常常在露天的高台上祭拜各种神灵。[34]在宗教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的融合也越来越明显。在该地出土的一个饰板图案上,大母神库柏勒(Cybele)正乘着一辆由几头狮子拉的车,驭手则是希腊的胜利女神;而另外一位女神的雕像完全是东方式的,正面直立,从脸形到服饰与希腊式神像有一定差别。[35]这些东方风格的神像在希腊人为主体的希腊式城市内出现,东方文化对希腊城市的影响显而易见。
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对印度的控制直到公元前200年之后才得以恢复。虽然分离时间很长,但印度西北部与希腊化王国的联系实际上并未中断。塞琉古王国和托勒密埃及的特使,如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和狄奥尼修斯(Dionysius)都曾到孔雀帝国访问。[36]同时,孔雀王朝还专门设立过一个部门,负责希腊人和波斯人的事务。除此之外,在阿育王的第2号法令(The Edicts of Asoka II)中,还提到了阿育王给边境之外的希腊人国王安条克及其相邻国王所统治的地区送去了草药。[37]在著名的13号诏令(The Edicts of Asoka XIII)中,阿育王就明确列举了其用佛法所“征服”的5位希腊人国王(事实上是派人传教),他们分别是Amtiyoko(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二世),Uramaye(埃及的托勒密二世),Amtikini(马其顿的安提柯·贡纳特),Maka(昔兰尼的马伽斯),Alikasudaro(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三世)。[38]不过,这很可能是一种出于宣传目的的夸大,目前没有明显的证据来证实早期佛教在这些地区有过传播,但是,相关希腊化国王名字能够在阿育王的诏令中出现,很显然是孔雀帝国和希腊化世界相互熟知的结果。在西方古典文献中也有类的记载,阿森纳乌斯(Athenaus)就曾提到孔雀帝国的国王宾头沙罗(Bindusra)曾向安条克一世索要一名哲学家和一些葡萄和无花果。[39]虽然,这则故事亦有虚构的成分,但是,与阿育王诏令中所出现的希腊国王名字一样,印度国王名字能够在西方古典文献中出现,也说明双方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东西方贸易往来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在塔克西拉的皮尔丘遗址(Bihr Mound),英国考古学家马歇尔(JohnMarshall)发现了一个孔雀帝国的钱币窖藏。其中混杂着三枚来自希腊化世界的钱币,两枚由亚历山大所发行,另一枚则是腓力三世(Philip Aridaeus,亚历山大的同父异母兄弟。他死后名义上的国王)发行。[40]同时,皮尔丘还出土了许多带有东地中海元素的艺术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雕版和印章,其中9—11号印章上主要雕刻了希腊的神灵和神话故事,包括雅典娜(Athena)、阿芙洛狄特(Aphrodite)、阿瑞斯(Ares)和小爱神厄洛斯(Eros)等,17—19号浮雕版上有一手捧飞鸟的女神,衣服却是埃及的风格。此外,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副耳环,两边的装饰是海豚的形状,据马歇尔考证,属于公元前3世纪地中海一带的工艺风格。[41]这种带有东地中海艺术风格的钱币和工艺品能够在塔克西拉出现,证明孔雀王朝与地中海世界保持着贸易往来。
除此之外,希腊文化和印度文化之间的互动融合也依然在进行。希腊语在孔雀帝国境内的大量使用就是证据。在阿育王所发布的诏令中,有的诏令用单纯的希腊语,有的用阿拉米亚文(Aramaic)和希腊语双语。双语诏令的出现,不仅证实了希腊人在孔雀帝国境内的存在,也证明这些希腊人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因为,阿育王要把这些看似简单的佛理说教译成标准的希腊语,传播给当地的希腊人,势必需要找到通晓两种语言的译者,这样的人才恐怕只能从希腊人或者是通晓希腊语的印度人中寻找。[42]此外,在坎大哈还曾经出土过一份以个人身份镌刻的希腊语铭文,其上讲述了自己因为家道中落,不得不到各地去经商,最后致富荣归故里,立碑纪念祖先的经历。根据雷切尔·梅尔斯(RachelMairs)的研究,这份铭文使用了很多荷马史诗中出现过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可见,作者受过非常良好的希腊语教育,但是,从作者名字上看,他和他父亲一样,似乎并不是希腊人。[43]
总的来说,在塞琉古王国治下,希腊式城市迅速恢复和发展,这为中亚和东地中海的交往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希腊化世界的主要贸易路线也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并为日后丝绸之路的贯通做了必要的准备。同时,塞琉古王国还积极发展与孔雀帝国的关系,客观上维持了和平局面,推动了希腊文化和印度文化的交流。
二 中亚与印度西北部的希腊化王国
(一)巴克特里亚-印度希腊人王国的兴衰
公元前三世纪中期,巴克特里亚总督狄奥多托斯一世(Diodotus I)宣布从塞琉古王国独立,[44]但两国间一度名义上还维持着主从关系。公元前208年,塞琉古王国安条克三世(Antiochos III)率军东征,在围困巴克特拉城近两年而不克的困境下,不得不与欧泰德姆斯一世(Ethydemus I)议和(前206年),客观上承认了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独立。塔恩还进一步推断,巴克特里亚王国很可能同时放弃了与帕提亚的同盟,转而发展和塞琉古王国的关系。因为,据波里比乌斯(Polybius)记载,欧泰德姆斯一世为了达成和安条克三世的和议,甚至还声称自己并没有从塞琉古王国独立,只是杀死了独立者的儿子而已。[45]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管理方式也基本仿照了塞琉古王国的模式,各地主要通过建立行省、任命总督的方式进行管理。
得益于当地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水资源,巴克特里亚王国独立以来,经济继续发展,国力日渐雄厚。从疆域上看,以阿姆河为中心的巴克特里亚地区是帝国的核心。环绕着这个核心,北边是索格底亚那,西边是与帕提亚接壤的马尔基亚纳和阿里亚的部分地区。在东方,欧泰德姆斯一世和其子德米特里一世曾向赛里斯(Seres)和弗里尼(Phryni)等地扩张[46],但是否进入中国的塔里木盆地,尚无定论。在南面,希腊人公元前200年以后先后在兴都库什山以南大规模扩张,主要有两次,一次在欧泰德姆斯和其儿子德米特里一世(Demetrius I)在位时期,一次在后来的印度—希腊人国王米南德时期。杨巨平曾对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向印度扩张的情况进行过梳理。[47]他认为德米特里一世对印度的征服路线主要是沿着亚历山大大帝的足迹,虽然远及旁遮普和印度河河口,但并未超出印度西北部的范畴,因为他本人要效仿亚历山大大帝,恢复希腊人在印度的遗产,在阿拉科西亚和印度河都有以其名字命名的城市就是最好的证据。至于其退兵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留守巴克特里亚的欧克拉提德一世(Eucratides I)发动叛乱,使其无暇继续南进。米南德一世对印度的征伐要比德米特里一世远,他是印度—希腊人中最有名的国王,其统治曾经覆盖到整个印度西北部地区。他尊崇佛教,对抗支持婆罗门教(Brahmanism)的巽加王朝(Sunga Dynasty)。除了重新控制西北印度以外,他还继续向东部进攻,甚至一度兵临华氏城(Pataliputta)下。他的钱币直到公元1世纪还在印度河口和巴里加扎(Barygaza)等地流通就是很好的证明。[48]
虽然与安条克三世的成功议和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巴克特里亚王国喘息之机,在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巴克特里亚王国一直维持着相对的繁荣和稳定,但外族入侵的危险却依旧存在。自欧克拉提德一世去世之后,巴克特里亚王国对属地的控制逐渐下降,北方的游牧部落也开始蠢蠢欲动。
有关外族入侵的历史更是零碎且充满推测。一般认为,较大规模的外族入侵大约有三次。分别是塞人(Sakas)、大月氏人和印度—帕提亚人(Indo-Parthians)的入侵。
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部落在蒙古高原上崛起,改变了当时“月氏势强而轻匈奴”的局面。从冒顿单于开始,匈奴人不断进攻大月氏部落,迫使大月氏人不得不向西迁徙。月氏人的这一次西迁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77—前174年间,从河西迁至伊犁河、楚河等塞地。受此影响,居住在此地的塞人不得不放弃故土,经费尔干纳谷地到达索格底亚那,然后到达巴克特里亚。他们很可能就是斯特拉波所说的参与灭亡巴克特里亚王国四部落之一的Sacarauli人。[49]不过,由于当时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尚有一定实力,所以这批塞人并没有全部占领此地,也没有在此地久留。这可能与大月氏人的尾随而来有关。
塞人出走后不久,乌孙王昆莫联合匈奴向大月氏人发动进攻,迫使大月氏人继续向西迁移。《汉书·张骞李广利传》中的“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说的应该是这一事件。[50]他们赶跑了先期到达的塞人,大约在公元前145年左右,征服了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塞人一部分“南越悬度”进入印度犍陀罗地区,一部分可能从巴克特里亚南下至阿富汗南部。[51]
除了塞人和大月氏人之外,第三股入侵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是印度—帕提亚人。早在米特里达特一世(Mithridates I 或称米特拉达特一世,Mithra dates I,约公元前171—前138年在位)时期,帕提亚人就控制了与巴克特里亚毗邻的马尔基亚纳和阿里亚地区,嗣后,借米特里达特二世(Mithridates II,约公元前123—前88年在位)反击塞人的军事行动,帕提亚人将国土扩张到了阿姆河流域。[52]公元前2世纪末,印度—希腊人王国因米南德的死去而逐渐分裂,这就给了外族入侵犍陀罗地区的机会。居住在塞斯坦的塞人首先经伯朗关(Bolan Pass)进入印度西北部,他们与之前经悬度而来的塞人一起,构成了所谓的“印度—斯基泰人”。[53]嗣后部分帕提亚人(他们也有斯基泰渊源)也从伯朗关进入印度。他们先进入了信德地区,然后由南向北向东逐步扩大自己的势力。[54]他们就是历史上的“印度—帕提亚人”(Indo-Parthians)。他们在此地的统治延续到公元1世纪末,结束于贵霜帝国向兴都库什山以南扩张之时。
(二)远东希腊化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由于材料的缺乏,有关巴克特里亚王国到贵霜帝国建立前的商贸与文化往来,只能依靠城市考古和出土钱币。其中,钱币方面的证据较为完整也较有说服力,显示出这一时期东西方的交流仍在继续。
自狄奥多托斯一世独立后,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钱币就打上了自身的标记,但仍然保持着希腊化钱币的基本特征。材质主要以银币为主,币制按照雅典的阿提卡银币为标准,一个德拉克马大约4.4克,四德拉克马重约17.5克,正面是国王的头像,背面是国王的保护神和希腊语铭文。在狄奥多托斯一世发行的早期钱币上,我们甚至还能发现安条克二世的名字。[55]虽然他这一做法实际上是个假象,表明自己还是忠于塞琉古家族,以此掩饰自己的独立,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巴克特里亚王国钱币与塞琉古王国钱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亲缘关系。
不过,随着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对印度西北部的征服,印度的元素逐渐在他们的钱币上出现。其中,国王头戴象头皮盔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种装饰与亚历山大有渊源关系。亚历山大生前就曾打造过雕刻着自己骑着战马和乘象的波鲁斯作战的纪念章以及带有大象形象的铜币。[56]亚历山大死后,托勒密一世发行过一种亚历山大头戴象头皮盔的钱币,以纪念他对印度的征服。[57]作为印度的新征服者,巴克特里亚国王德米特里一世也效仿了这种做法,钱币上的形象也是头戴类似的象头皮盔,[58]似乎也在宣示自己对印度的征服。可以说,这一做法拉开了希腊式钱币和地方文化相融合的序幕。
自德米特里一世开始,印度宗教的元素开始出现在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钱币之上。希腊人对印度神和宗教观念的认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阿伽托克勒斯(Agathokles)和潘塔莱昂(Pantaleon)为代表,他们逐渐将印度神或宗教引入其钱币和宗教崇拜之中。但涉及具体的印度宗教观念仍以图像暗喻的方式出现。如用狮子、菩提树、佛塔表示佛陀或佛教。第二阶段以印度—希腊人国王米南德为代表,除了继续使用单一隐喻性符号表示对印度神和宗教观念的接受外,他的钱币上开始出现了希印对应的隐喻符号,如象头/木棒型(表示佛陀与赫拉克勒斯)、公牛头/三脚架(表示湿婆 Siva 与阿波罗 Apollo)、法轮/棕榈枝(表示佛法与胜利、和平)。这就表明,这时的希腊人不仅接受了印度的神和宗教观念,而且还有意识地把他们与希腊的神和宗教观念相等同。[59]
当地文化对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影响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双语币的出现。这种钱币最早由潘塔莱昂和阿伽托克勒斯所发行。最初的双语币一面是希腊文,一面是婆罗米字母(Brahmi),虽然语言不同,但内容一致,后者基本是前者的对译。以阿伽托克勒斯发行的双语币为例,该钱币为方形印度币,正面是婆罗米字母铭文“国王,阿伽托克勒斯”(Rajane Agathuklayasa),背面是希腊语的对译“ΒΑΣΙΛΕΩΣ ΑΓΑΘΟΚΛΕΟΥΣ”。[60]与之相似,潘塔莱昂的双语币也是方形币,正面是婆罗米字母铭文“国王,潘塔莱昂”(Rajane Pamtalevasa),背面是希腊语的对译“ΒΑΣΙΛΕΩΣ ΠΑΝΤΑΛΕΟΝΤΟΣ”。[61]后来,这种双语币被广泛仿制,只是婆罗米字母逐渐被佉卢文所取代。可以说,这种类型钱币的发行,既表示了希腊人对当地语言的认可,又宣示了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还方便了这种钱币在当地的流通。
到了印度—斯基泰人和印度—帕提亚人统治时期,双语币已成常态。从印度—斯基泰人的钱币上看,它们基本承袭了阿波罗多托斯二世(Apollodotus II)等印度—希腊人国王的货币体系,以德拉克马和四德拉克马作为标准,钱币的正面为希腊语,反面为佉卢文。从图像上看,正面依旧是国王头像或国王骑马像,背后大部分是希腊的神祇。以阿泽斯一世(Azes I)的部分钱币为例,该钱币的正面是国王(可能是宙斯神)手持长矛,背面是手持橄榄枝的胜利女神尼科(Nike)。在钱币的边缘,正面是希腊语的“王中王,伟大的阿泽斯”(ΒΑΣΙΛΕΩΣ ΒΑΣΙΛΕΩΝ ΜΕΓΑΛΟΥ/ΑΖΟΥ),背面是佉卢文的对译(Maharajasa RajarajasaMahatasa/Ayasa)。[62]这很显然就是承袭印度—希腊人双语钱币的模式。不过,由于游牧民族并不完全熟悉希腊钱币的制作工艺,其银币的制作相对粗糙,重量也较之前有了一定的下降。以法国钱币学家波比拉赫奇提供的印度—斯基泰人国王毛厄斯(Maues)的银币为例,其发行的四德拉克马银币的重量已经降到了10克左右,而部分一德拉克马的银币甚至降至1.55克,[63]印度—帕提亚人的钱币也同样采用双语。控制阿拉科西亚的贡多法勒斯(Gondophares)及其后继者们也发行过双语钱币。以贡多法勒斯的钱币为例,正面是其本人的头像,反面是胜利女神尼科,正面的希腊语铭文写着类似的“王中王,伟大的贡多法勒斯”(ΒΑΣΙΛΕΩΣ ΒΑΣΙΛΕΩΝ ΜΕΓΑΛΟΥ/ΓΝΔΟΦΕΡΡΟΥ),后面的则是佉卢文的对译(MaharajasaGadanasa nisadasa hinasa vanidasa javati devavrata),[64]这很显然也是对印度—希腊人钱币的一种模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和印度—希腊人钱币上的王衔,印度—斯基泰人和印度—帕提亚人钱币上的王衔要更丰富,其中常常会出现“王中王”,(希腊语ΒΑΣΙΛΕΩΣ ΒΑΣΙΛΕΩΝ,佉卢文Rajarajasa)的这样称谓。有关这一称谓,很可能最早来自亚述。据说亚述王图尔库蒂·尼努尔塔一世(Tukulti-Ninurta I)就曾经拥有这一头衔。[65]后来,这一头衔被波斯人所接受,在著名的贝希斯敦(Behistun)铭文上,大流士一世就拥有这一头衔。[66]帕提亚人从密特拉达特二世(Mithradates II)起,开始在钱币上使用这一头衔。这种双语币,日后也被贵霜人所吸收,成为贵霜钱币,甚至丝路钱币中最为普遍的一种类型。
除钱币之外,这一时期东西方交流的另一大证据来自城市考古。在中亚,伴随着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扩张,城市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巴克特里亚有“千城之地”的美名,[67]除阿伊·哈努姆以外,一些新兴的城市在巴克特里亚王国时期也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如阿姆河的渡口要塞坎培尔·特佩(Kampyr Tepe,属于铁尔梅兹古城遗址的一部分),后来成为贵霜帝国都城之一的高加索的亚历山大里亚,位于木鹿绿洲的马尔基亚纳的安条克城,阿拉科西亚的亚历山大里亚,索格底亚那地区的马拉坎大等。这些城市大部分都是以原来希腊人所建的军事据点为基础,或者在原来城市的基础上重建。
以著名的铁尔梅兹遗址(Termez)为例,该城位于阿姆河北岸,由数座小型遗址所构成,法国学者勒里什(P.Leriche)猜想它可能就是亚历山大所建的阿姆河畔的亚历山大里亚(也有不少学者认为阿伊·哈努姆遗址才是阿姆河畔的亚历山大里亚)。希腊化时代的遗存主要集中于坎培尔·特佩遗址。其中,希腊化陶器层厚达两米,陶器的风格与阿伊·哈努姆遗址出土的陶器大致相同,显示二者当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联系。不过,由于该地原为希腊—马其顿人驻防的渡口所在地,也具有防御的功能,它当时距离阿姆河仅有20米(由于河流改道,现在已经相距甚远),该选址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更好地观察并控制阿姆河沿岸。[68]
中亚希腊化城市的发展势头,并未因之后的外族入侵而放缓。据张骞,大夏“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69]可见,在大月氏人征服巴克特里亚之后,该地的城市并未因大月氏人的入侵而毁灭,相反,通过近代以来考古学者的努力,当时的一些新兴城市正逐渐被人们所熟知。例如卡尔恰扬(Khachayan)、达尔弗津·特佩(Dalvezin Tepe)、第伯尔金(Diberjin)、塔赫特-伊·桑金(Taht-i-sangin)等。它们为后来贵霜帝国中亚城市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希腊人是中亚希腊式城市中的居民主体。在阿伊·哈努姆遗址就曾经发现过一则公元前150年前后的希腊语铭文,它刻在一尊雕塑的石头底座上,雕塑本身已经毁坏,但铭文得以保存,其上写着“特利巴洛斯和斯特拉通诺斯,斯特拉托斯(之子),(献给)赫尔墨斯和赫拉克勒斯”(Τριβαλλòς καì Στρáτων Στρáτωνος ρμη ι-ρακλε ι-)等字样。赫尔墨斯(Hermes)和赫拉克勒斯是希腊体育馆的保护神,可见当时的希腊人还在使用这个体育馆。[70]
ρμη ι-ρακλε ι-)等字样。赫尔墨斯(Hermes)和赫拉克勒斯是希腊体育馆的保护神,可见当时的希腊人还在使用这个体育馆。[70]
当地人已经在巴克特里亚王国城市人口中占据了一定的比例。从考古发掘上看,在阿伊·哈努姆遗址曾发现过两份公元前2世纪的羊皮纸货物单据。一份残缺严重,一份尚可阅读。较为清晰的那份单据上断断续续用希腊语写着“安提玛科斯30年……于K.arelote附近的安菲波里斯城生产……属于40……雇佣兵……斯基泰人,100德拉克马银币……以上所提及的……总计……”[71]从内容上看,这份单据很可能是巴克特里亚王国国王赐予包括斯基泰人在内的外族雇佣军的赏赐。此外,阿伊·哈努姆遗址还保留了不少题铭,其中部分题铭者的名字具有伊朗文化的特征,如Oumanes、Xatranos等。[72]这些类似伊朗人的名字清楚地表明,在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城市中,希腊人和当地人混居的现象十分普遍。
城市的发展带来的是商贸的繁荣。在现代巴林和古代苏萨的遗址就曾出土过巴克特里亚王国国王欧泰德姆斯一世、欧克拉提德一世和赫利奥克勒斯(Heliocles)的钱币。[73]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黄金之丘”。该遗址位于阿富汗北部,由7座大型墓葬组成,由于遗址中找不到明显的城市的痕迹,所以学界认为其很可能是尚在游牧的大月氏人驻地或者是早期贵霜人的墓地。该墓地共出土大约两万件珍贵的黄金制品,包括刻有希腊雅典娜图案的戒指、巴克特里亚风格的阿弗洛狄特雕像、中国的铜镜和草原风格的双兽头手环等。[74]尤其是在“黄金之丘”的3号墓,学者们还发现了一枚帕提亚银币和一枚罗马的金币,[75]以及来自印度的5块象牙雕版残片、两个象牙骨灰盒和印度的带狮子图像的金币等。[76]这些证据说明,即使是在大月氏人到达中亚后,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也根本没有中断过。张骞提到的中国的邛竹杖和蜀布,经印度转手,最后出现在大夏市场,《汉书·西域传》中说大夏人“善贾市,争分铢”,[77]显然都是有据可依。
兴都库什山以南的情况与中亚类似。从城市的布局上看,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希腊城市依旧保留着其原有的风格。以塔克西拉的斯尔卡普(Sirkap)遗址为例,该城的格局从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建城之后,就没有太大的改变,一直存在到贵霜时期。在塔克西拉遗址的诸多建筑物遗存中,最能代表这一时期艺术风格的莫过于斯尔卡普遗址附近的詹迪亚尔(Jandial)神庙。根据马歇尔的考证,该神庙是一所琐罗亚斯德教的神庙,但是建筑的风格属于典型的希腊风格。它分成前厅、圣堂和后门厅三大部分,这一布局与雅典的帕特农神庙(Parthenon)颇为类似。[78]虽然,詹迪亚尔神庙用密封的围墙替代了希腊式的围柱,只在前门保留了两根爱奥尼亚风格的石柱。但是,该神庙的屋梁、雕塑和檐饰等装饰依旧保留着希腊的风格,这体现出了建造者对希腊建筑艺术的模仿。同样的模仿也出现在塔克西拉当地艺术品的风格上,在斯尔卡普遗址的印度—斯基泰人地层中,就曾经出土过一些石雕和石器,包括6个装饰人物、动物形象浮雕的化妆盘和一个女性小圆雕。按照马歇尔的说法,虽然这些雕塑属于希腊的风格,但是其制作工艺相对粗糙,很可能是犍陀罗当地的工匠们对希腊风格艺术品的模仿。[79]
不过,与中亚地区不同,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希腊化城市中有不少佛教建筑出现。以塔克西拉为例,它在阿育王时期就是一个重要的佛教中心,印度—斯基泰人和印度—帕提亚人将该地的佛教建筑基本保留了下来,并使之继续发挥其宗教功能。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位于斯尔卡普遗址的一处佛塔。[80]同时,相关的铭文也证明佛教活动在印度—斯基泰人和印度—帕提亚人统治时期的频繁。出土于塔克西拉的一块铜锭上就记载过当时修造释迦牟尼舍利塔和僧伽蓝以供诸佛的情况;[81]秣菟罗(Mathura)的狮子柱铭文也提到过秣菟罗总督的妻子向当地的佛寺奉献礼品及安放佛陀舍利的情况。[82]可见,在印度—斯基泰人和印度—帕提亚人统治时期,佛教实际上还在继续发展,这就为以后贵霜帝国时期佛教的繁荣和大乘佛教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从出土文物上看,该地区与地中海世界的商路是畅通的。在塔克西拉的斯尔卡普遗址,马歇尔就发现了不少希腊或者地中海风格的产品。其中包括一个希腊风格的盘子,用失蜡法做成的油瓶,以及大量的玻璃珠子。[83]这些文物显然不是出自印度工匠之手,很可能来源于与东地中海沿岸地区的贸易。此外,马歇尔曾对塔克西拉遗址出土的欧泰德姆斯和阿加托克勒斯钱币进行过分析,他认为,这些钱币中含有一定量的镍元素,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并不产镍,所以他推断造币用的镍金属很可能是来自于中国。[84]到了公元前100年前后,随着印度洋季风规律的发现,从埃及或阿拉伯直航印度成为可能。斯特拉波曾经提到,当时的商人们从埃及经尼罗河和阿拉伯湾航行到印度,远至恒河流域。[85]在所有相关的文献中,成书于公元1世纪前后的《厄立特里亚航海记》特别值得关注。该书主要记录的是从红海到印度的主要航路以及沿线的港口及其进出口的货物。其中提到,从赫莱亚(Horaia)出发,经过一个不知名的有皇家宫殿的地方,就到了斯基泰人(即印度—斯基泰人)的海岸,该地的主要海港就是巴巴里库姆(Barbaricum),货物从这里上岸,然后被运到附近的都城Minnagara。此外,该书还记录了大量用于贸易的货物,它们来源丰富,并非完全出自印度地区。其中,丝线、丝绸织品、皮革、玛瑙、水晶石、绿松石、天青石各种宝石,其产地应该是中国、中亚草原和阿富汗;苏合香、乳香等应该是来自阿拉伯半岛;葡萄酒可能来自意大利半岛和叙利亚地区的劳狄西亚(Laodicea,今拉塔基亚,Latakia);罗马钱币、粗玻璃、珊瑚、亚麻布等是从地中海地区、埃及等地运来。[86]这也在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印度—斯基泰人和印度—帕提亚人统治期间海上贸易的繁荣。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无论是巴克特里亚地区还是印度西北部,都没有因为巴克特里亚的独立或游牧民族的入侵而衰落。相反,无论是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印度—希腊人还是新入侵的游牧民族,他们都在积极发展经济与贸易,从而推动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在南线,从埃及到印度的海上直航已经实现;在东方,张骞的两次出使和汉武帝的反击匈奴,从玉门关到河中地区的道路基本开通;在西部,帕提亚的米特里达特二世正励精图治,积极反击塞人;在中亚十字路口的巴克特里亚和西北印度,一个强有力的帝国即将出现,它就是与罗马帝国、帕提亚帝国和汉帝国并立的贵霜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