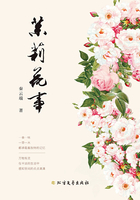
凤仙花和花梗股
去做美甲,发现费用又涨了,还未开口提意见,店主就掐掉了我的“不良”念头:“现在人工很贵的,技师很难找的,材料只涨不跌,我们又只用最好的材料……”千篇一律的说辞。意识到提意见没用,我就闭嘴了。美甲不是民生必需品,不像猪肉、大米、水、电,那都是关联老百姓神经的,涨几块钱要掀起轩然大波的。美甲这事儿,不接受涨价可以选择不做,这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
突然怀念起了小时候用指甲花染红指甲的趣事。指甲花染出的指甲,肉红肉红的,还挺自然。现在去做美甲,我一般也选用低调的颜色,如肉色、藕色,不喜欢很艳丽或者跟装束反差极大的颜色,不然看起来跟九阴白骨爪似的。
小时候的指甲花,大名凤仙花。要说别名,可多了去,除了指甲花、指甲草之外,还有小桃红、金凤花、透骨草、急性子、鸡爪子花、女儿花、小点红、假桃花、芰芰草、洒金花……别名多得令人咋舌。这几个名字中,我最喜欢“小桃红”,话音未落间,脑海中已浮现出一个娇俏动人、红唇乌眸、皮肤嫩得能掐出水来的妙龄女子。
别名金凤花,这个好理解,取之于凤仙花的形态如展翅欲飞的金凤凰,这在古代的诗词中多有见证。明代诗人瞿佑《凤仙》诗云:“高台不见凤凰飞,招得仙魂慰所思。”是把凤仙花比喻成凤凰的仙魂,以慰藉人们对凤凰的崇拜与思念。唐朝吴仁壁亦有《凤仙花》诗:“香红嫩叶正开时,冷蝶饥蜂两不知。此际最宜何处看,朝阳初上碧梧枝。”传说中的凤凰是栖身在梧桐树上的,百鸟之王非梧桐不栖,别看现在梧桐树、凤仙花这么平民化,在古代的花卉史中,可也算是高贵的!
那为啥又叫“急性子”呢?这跟凤仙花的种子有关。对于凤仙花的种子,小时候的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出它为何如此之奇妙?种子成熟时,只要轻轻一碰,它竟然像个弹弓似的弹开,果皮突地向内蜷曲,裂成几瓣,里面的黑色籽儿便喷撒而出,仿佛情急意切地要离开这个果皮包起来的“小房子”,真真是个急性子!在英文中它叫“Touch Me Not”——别碰我。
在那个玩具奇缺的年代,捏凤仙花的种子,成了我们其乐无穷的游戏之一。越是成熟的种子,弹裂得越带劲儿,手指轻轻一碰,神奇立现。于是下午放学回家的我,边走边寻找可以捏的凤仙花种子,捏到成熟的种子,就像发现了宝贝似的欣喜异常;捏到不够成熟的种子,唉声叹气,满心失望。直到长大后,生物课上讲到凤仙花种子的传播方式,才知道那术语叫“弹射传播”。
凤仙花还有一个别名“菊婢”,对于这种称呼,其实我是拒绝的。它来源于宋朝张耒一首《菊诗》:“金凤为婢妾,红紫徒相鲜”,明显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凤仙花嘛!凤仙花虽无秋菊的傲霜风骨,却也有自己的妩媚之处,红似鹤顶,花如凤舞,别有风韵。落地生根,更是一种顽强生命力的体现,何必又拿贬低它来抬高菊花呢?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胸怀和见地就完全不一样。毛主席在少年时代写过一首《咏指甲花》诗云:“渊明独爱菊,敦颐好青莲。我独爱指甲,取其志更坚。”在少年毛泽东眼中,这种不择土壤、随处能够生长的花,傲暑盛开,不是卑贱,而是一种顽强意志的体现。当时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要他去学做生意,他却立志要走出韶山冲去外地求学。少年毛泽东出身草根,却志向远大,心中怀有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抱负,可真应了“金鳞本非池中物”一说。
小时候拿凤仙花染红指甲,还得是偷偷地,怕被父母知道,被斥责为臭美、“拾野魂”(思想走火之意)。等暑假去了奶奶家,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臭美了。奶奶还教我怎么染色:摘了大红或紫红的花瓣,加点盐巴捣烂,敷在指甲上,然后用叶子包住指甲,用线把指甲包扎起来。晚上包好,第二天醒来,指甲就能变红了。当然,这都是小孩玩的新鲜事儿,经常出意外,晚上睡觉没睡相,早上醒来时,指甲花早就散了一床,指甲没染红,指头倒是被丝线勒得皱巴巴的。总之就我个人经历来看,成功率少之又少,要是成功了的话,那能美上一整个夏天。
不是我在为自己的臭美找依据,用凤仙花染甲的历史,是大有渊源可追溯的,古今中外亦如是!印度人称凤仙花为HENAA,用它做身体彩绘的染色材料。中东人也很早就种植了凤仙花,取其汁液染甲或修饰容颜。比如那个大名鼎鼎的埃及艳后,就曾经用指甲花来染头发,那位可是臭美界的鼻祖了,牛奶、葡萄酒、酸奶、金箔、死海的泥巴、骡马的粪便……什么都能被她敷上脸敷上身,而且是全天然的,后人只有膜拜的份儿。在中国古时的臭美年代唐朝,美甲得到了盛行,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有钱的贵人戴起金属假指甲来显示尊贵地位,平常人家也争相用凤仙花染甲求美。唐朝诗人李贺在《宫娃歌》一诗中描写了当时宫中女子对烛染指、“花房夜捣红守宫”的场景。宫中女子旷日无事,温饱无碍,每日想的无非是如何与他人竞美,如何从三千粉黛中一跃而出,有朝一日老天开眼得见君王以改变命运。所以我们不妨想象在那个凤仙花盛开的季节,各种风情、各种媚态如画卷般铺展而开,美人们手如柔荑,在点点红甲的映衬下,有抚琴的、捻香的、抹鬓的、托腮的、凝眉的、执扇的、掀帘的、拈花的、拂柳的……简直就是一幅幅令人心旌动荡的应时风情长卷。
凤仙花颜色很多,除了我们通常用来染甲的大红和紫红,据说还有一些名贵品种,如洒金,说实话洒金我没有亲眼见过,听名字显得颇为金贵稀有。我见过五色的凤仙,其花瓣五色相杂,与传说中凤凰“羽毛五色,声如箫乐”倒是不谋而合了。还有一种白色凤仙花,不得不提。不提它,就对不起咱华夏博大精深、海纳百川的美食文化了!
在我们老家,白色凤仙花的梗,会被腌起来制成下饭的咸菜,方言称其为“花梗股”。做法是将白色凤仙花的茎切成四五厘米的长段,于沸水中焯熟,然后清水浸泡,每天换三四次水,数日后,花茎的苦涩味才能彻底去除。然后滗去水,拌入盐,腌它个一天一夜,咸味就进去了。这还不能吃,得把花梗股转移到坛子里去,再加冷却的盐开水腌制四五天,才算成。腌好的花梗股味道清爽,吃的时候,用嘴咬着花茎的管子,哧溜哧溜把里面咸咸鲜鲜的汁液吸出来,特别在夏日炎炎食欲不振的时候,花梗股过清粥,味道可好了!
以前园子里凤仙花长得一片片的,不去打理,它们都能自己越长越旺。长得差不多了,大人们就去收割了来,腌制花梗股,仿佛是老天馈赠给我们的特别食物。后来,我们搬到了父亲学校的宿舍居住,渐渐失去了与凤仙花的机缘。我也曾经跑到后山上寻找,发现大多是后山住户自己拓了一片地种植的,不能去收割了。再到后来,后山上也不见了它的踪影,只在菜场里偶尔遇见有人卖自家腌制的花梗股。再后来,菜场里也不见了它的踪影……夏天的时候,有时会跟母亲唠叨起花梗股,说这好吃的下饭菜就这样失传了吗?
就这么渐渐淡忘了小时候伴我们长大的味道,后来成了外地人,口味更是渐渐产生了更大变化。一年又一年,直到有一天……它突然又出现了,带给我无比的惊愕与惊喜。那是在杭州一家餐厅里,它与臭豆腐一起,以“蒸双臭”的名号隆重登场,红火了好一阵子。我当时就震惊了,大声说“这不就是小时候的花梗股吗?你们知道吗?”在场的所有人一脸茫然。他们见我的神情仿佛是遇见了一个久别重逢的老友般兴奋,都十分不解。唉,他们是不了解我跟花梗股以前许多美好的故事和秘密的!看着精致盆子里的“蒸双臭”,花梗股静静躺在那里,不言不语,让我觉得熟悉又陌生,又有些伤感。
小花瓣儿、红指甲、夏日的凉席、天真的娃……那是永不能复制的童年了。
2016.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