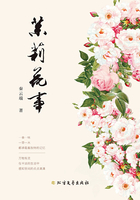
我爷爷
(一)
印象中,我爷爷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我从没见他笑过。可是我却一点也不怕他。我能记事的时候起,他已经很老了,年近八十,整天躺在床上,吃饭也在床上。有时候会坐起来看看报纸,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直挺挺地躺着,面无表情,口中不时发出长长的吐气之声。我搞不懂他为什么会发出那种奇怪而有规律的声音,于是总是纠缠着奶奶问为什么?奶奶解释不了,现在想来,那不过是爷爷长年累月以来的习惯罢了。
爷爷身材高大,十分清瘦,似乎全身只是一层皮肤包着骨头,乍一看像病入膏肓,却也一直没有上过医院,因为后来也没有生过什么大病。据说年轻的时候曾经得过肺病、吐过血,“文革”期间为了躲避迫害,干脆就装病在床,长卧不起,渐渐养成了习惯。听说爷爷对我的父亲特别严厉。奶奶告诉过我一个故事:我父亲小时候十分顽皮,有一次爬上床头,偷吃了铁皮罐里的炒米糖。爷爷知道了,把他狠狠揍了一顿,并让他待在矮墙头上以示惩罚。为此奶奶十分心疼,她认为小孩贪吃是天性,偷吃一块炒米糖没什么大不了的,但爷爷认为家规就是家规,女人休得多嘴。奶奶自然不敢再多言。我一向认为爷爷比较偏爱我大伯,觉得大儿子为人稳重、老成,而我父亲小时候顽皮无知,自然少不了“吃柴”。
尽管日常生活中长卧不起,但人有三急,他也得起床如厕。奶奶对我说,你别看他老躺在床上,走起路来,像风一样!于是我特别仔细地观察,果然是十分利索,虽然用风来形容过于夸张,但因为他身材高大,步子跨得大,所以走起路来给人衣襟带风的感觉。
爷爷有双奇怪的耳朵,这双耳朵似乎只听得见好话,而听不见坏话。家里来了乡下亲戚,奶奶就坐下来陪人家唠家常,当然也会抱怨日子的不顺,爷爷耳朵就聋了,似乎没听见有人在聊天,只是象征性地朝客人点下头以示招呼,然后就面无表情,仿佛老僧入定了一般。客人觉得被忽视,自然有些尴尬,奶奶就跟客人解释说:他耳聋已经好久了!但当大家谈得兴起,说到他以前的辉煌往事的时候,他似乎又听到了大家谈话的内容,在床上也辗转反侧起来,嘴里评论起来,于是奶奶又跟客人们解释说,只要讲他的好话,他耳朵就不聋了!引得大家哄然大笑起来。
(二)
我爷爷一生有两任妻子。第一任妻子,也就是我大伯的母亲。这其中有个悲惨的故事,因为听说第一任妻子是被他惩罚死的。从小我就对这个说法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后来我长大成人、成家立业,有了孩子,更加不愿意相信这个故事。但家族亲戚中有年长的前辈却坚持这个说法。据他们说,那个女人因为触怒了爷爷,被整夜罚跪在天井中,半夜时分下起了雨,女人因此受了风寒,从此一病不起,医治不愈,直到离开人世。假如这件事是真的,那真是封建社会婚姻制度中男尊女卑所造就的一个巨大惨剧!然而经我观察,并没有感受到大伯父对他父亲有什么怨恨,那些描述此事的亲戚们,也并没有带着慷慨激昂的情绪,反而是带着一种无比敬畏的神情去描述这个事情,这更巩固了爷爷在后辈们心中神秘而威严的形象。
我从小几乎是奶奶带大的,奶奶只有我父亲一个儿子,没有孙子,虽然感觉十分遗憾,却也退而求其次,对我这个长孙女宠爱有加,甚至可以说是溺爱了。自从我有认知能力开始,发现爷爷并没有对奶奶有特别严厉的迹象,根据那些爱闲话家常的亲戚们的说法,他这是因为觉得自己做了错事而心中愧疚,因此对第二任妻子态度好了许多。对于这些议论,爷爷自始至终保持沉默,他从来也没有向我提起过任何往事,仿佛那一切都已经尘封在记忆的密匣之中,再也不会被打开。从小我读了很多儿童文学,故事中爷爷的形象总是和蔼可亲,他们会在黄昏的傍晚,坐在庭院、村口,给后辈们讲述往事,其乐融融。而我的爷爷,却像一块沉默的长满青苔的石头,虽然对我并不严厉,却从来话语无多。
(三)
“就着美孚灯昏暗的灯光,爷爷在墙板壁上给我变幻出各种各样的手影。他是个严肃的人,但这时候,他会柔和而宽容地看着我,而我则乐得像个开心果似的笑着,然后他就更加卖力地变幻出新的花招来。”
我那当年贵为北大历史学教授、精通多国语言、有幸曾与我们毛主席共事过的爷爷,最终在“文革”中被挂破鞋上街游行,因此不得不装病以躲避迫害。爷爷卧床长达数十年后去世正好赶上火葬推行,一把怨骨化成黄土飞扬不知所终。曾经一把大火烧掉了九曲巷的老宅。记得那里有张雕花镂空的大眠床,通体漆成了棕黑色,按照老说法,应该是“九进眠床”。当然,跟现代的床不好比。这张床,上楣是连续的陶瓷童子嬉戏彩画,两侧床楹是镂空木雕外加陶瓷片,上面写着“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诗句。床后围正中是一面长方形的镜子,因年代久远,镜子十分模糊,并且水渍斑斑。当年的很多古床都装着大镜子,不知这是为何?这在现在,于我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当地有个迷信的说法是镜子不能对着睡觉的人,说那样杀伤力十分之大。以前我杭州家里的柜子上有两面穿衣镜,自从老母亲指出镜子杀伤力大之后,我晚上睡觉都不安稳,仿佛感觉有凌厉的刀气,从镜子里射出来一样。后来,还是把这柜子撤换掉了。
言归正传,当年爷爷旧宅的堂前还有八仙桌、长板凳,小小的我坐上去之后脚尚够不到地面,于是两脚不停地晃荡晃荡,悠闲有乐趣。屋子里还有数个棕黄色的牛皮箱,上敲大印“永泰隆”等店号。堂前的屋檐好高,下雨时,滴滴答答的雨水从屋檐坠落下来,有时像珠串,有时像银线,接雨水、看天空成了我自得其乐的游戏之一。这些记忆的碎片,仍然是那么清晰、生动。只可惜后来一场大火,将这一切的安静美好,都凝固成了脑子里的一张黑白旧照。
大火之后无家可归,住在朋友素青姐家里大半年后,爷爷奶奶搬到了三井巷一个沿街的小屋子里。小屋子的地是泥地,由于长期的走动,泥地被磨得光滑而结实,我常常需要拿铁棒才能撬出一个小洞来。潮湿的季节,木头柱子边上会长出小蘑菇来,对于年幼的我来说,简直是一个有趣的奇观。房间里摆两张床,一张好一些的床给爷爷躺着,还有一张木板搭成的所谓的“床”,是奶奶用的,我来的时候,就和奶奶挤在这张木板床上。有一次,半夜里奶奶掉到床下去了,那会儿她刚被自行车撞了,腿受了伤,爬不起来,为了不影响我睡觉,一整个晚上就躺在泥地上,直到我第二天睡醒,她才叫我把她拉起来。现在想起这些事情,热乎乎的眼泪还会不听话地夺眶而出。
爷爷有两个从大火里抢救出来的皮箱,一个皮箱里装着皮袄子,我母亲说那叫“皮统”,听起来很唬人的样子,其实现在看看都是很粗糙的东西,里子上的毛硬得可以当板刷。老一代人把这些皮袄子当成传家宝,隔三岔五地拿出来翻一翻、晒一晒,免得被虫蛀了,至今我母亲还在不厌其烦地“照料”着上一代传给她的数件“皮统”。另外一个箱子里装着些旧书,包括爷爷当年的校友录,还有他翻译的文稿等,这些是比较珍贵的。这箱子里还有奶奶从大火里抢回来的一些首饰,装在一个圆肚子的玻璃瓶里,这是最最让我好奇的东西了,女孩子对首饰的喜爱,是与生俱来不用教导的。箱子上用那种古老的挂锁锁着,我常常要缠着奶奶打开箱子,拿出玻璃瓶来,一件一件摆弄那些珍珠玉石做成的花花绿绿的头饰和首饰。现在我回老家,偶尔母亲打开老箱子,我还是会看到这些东西,只是现在的心境确实完完全全不同了,会感到哑然失笑。这些做工和材料都很粗糙的东西,当时却是多么地膜拜它们啊!
201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