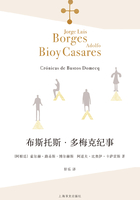
第5章 更新版自然主义
当证实了富有争议的描述主义—描述性主义不再非法占据各个文学增刊以及其他简报的首页时,不得不说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任何人——在西普里亚诺·格罗斯(S. J.)的严谨教导之后——都不可能再忽略,刚才所提的第一个词语在小说领域真正被运用起来时,第二个词语则被抛向了各种其他文类,这其中甚至还包括诗歌、造型艺术以及评论文章。然而,概念的混淆仍旧一直存在,在喧嚷的真理爱好者面前,乌尔巴斯的名字也会和博纳维纳的名字套在一起。也许是为了把我们从如此严重的错误中引开,不乏有人作下另一种恶,拥护起另一种可笑的结合:伊拉里奥·拉姆金—塞萨尔·巴拉迪翁。我们就承认吧,这类混淆的基础是些许表象的相似和一部分术语的相像;尽管如此,对于经受过严格训练的读者来说,博纳维纳的一页文字永远都是……博纳维纳的一页文字,而乌尔巴斯的一册书永远都是……乌尔巴斯的一册书。事实是,外国的文人们散布一种关于阿根廷描述性主义流派的流言;我们所做的,则是反复阅读一个可能存在的流派的耀眼名作,并依靠由此获得的有限权威性确认了如下结论,即刚刚所提及的并不是某种重要的核心运动,更不是某个文艺人士的聚会,而是一项个人与众人的创举。
让我们来深入领会一下其复杂的内在吧。想必你们已经猜到了,在进入这个充满激情的描述性主义的小世界时,第一个与我们握手的名字是拉姆金·弗门多。
伊拉里奥·拉姆金·弗门多的命运着实奇妙。那时,他的作品大多很短,不太能引起普通读者的兴趣,他会把这些作品带到某个编辑部去,那里的编辑都视他为客观的评论家,也就是说,一个在其评注的作品中既不褒扬亦不贬损的人。很多时候,他对书籍的“短注”会缩减为谈论封面和腰封的陈词滥调,随着时间推移,甚至具体到了书本的样式,长宽厘米数、单位重量、印刷工艺、墨水质量、纸张的孔隙率以及味道。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九年,拉姆金·弗门多一直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年报》的尾页撰稿,既没赢取赞誉,也没获得批评。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他拒绝了这份工作,以便全力以赴地投入一项对《神曲》的批评研究中。死亡在七年之后降临,彼时,他的三卷巨著已交付印厂印刷,它们将成为且如今已成为他名誉的基石,这三卷作品的题目分别为:《地狱》、《炼狱》、《天堂》。公众对此并不理解,他的朋友们更不明白。当时,不得不请出一位姓名首字母为H. B. D.[8]的德高望重的人物来维持秩序,使布宜诺斯艾利斯揉揉惺忪的睡眼,从自己教条的梦中醒来。
根据极有可能属实的H. B. D.的假设,拉姆金·弗门多曾在查卡布科公园的报亭中翻看过十七世纪的那本无足轻重的小书:《谨慎男子之旅》。该书的第四册介绍道:
在那个帝国,地图绘制技艺已达到完美纯熟的程度,一个省的地图可以铺满一座城,帝国的地图则可以占据整个省。渐渐地,这些过分巨大的地图也不再能满足人们,制图院于是便绘出了一幅帝国地图,与帝国本身大小相同,其余一切也都与之完全相符。他们的后人不再疯狂迷恋地图的绘制,明白那辽阔的图纸毫无用处,便冷酷无情地将它交付给了酷日与严冬。在西部的沙漠中,仍有残存的地图遗迹,被动物和乞丐当作了居所;除此地之外,帝国境内再没有其他地理学科的古迹了。
拉姆金依靠自己一贯的洞察力,在一众友人面前指出,与自然尺寸相同的地图虽然有严重的问题,但类似的方法却也不是不可以推行到别的学问上,评论文章便可成为一个例子。从那个恰当的时刻起,绘制一张《神曲》的“地图”便成为了他生命的意义。最初,他很高兴能用简短的、不全面的陈词滥调写出地狱各个圈层、炼狱山,以及九重同心天的概况,作为边角料装饰蒂诺·普洛文萨尔所出的颇受赞誉的版本。然而,严于律己的天性令他无法因此而满足。但丁的诗歌总是从他手中溜走!第二次得到了启示之后,他很快就开始用费力而绵长的耐心将自己从短暂的迟滞中拯救了出来。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他的直觉告诉他,对诗的描述若想达到完美,所用的单词应该与诗中的每一个单词都一致,就像那张与帝国完全一致的地图。成熟的思考后,他删掉了前言、注释、目录,以及编辑的姓名与地址,将但丁的作品交到了印厂。就这样,第一座描述性主义里程碑在我们的首都揭幕了!
眼见为实:不乏有书虫把这被评论界视为最新壮举的作品当成或假装当成但丁名诗的又一版本,将它作为原著的读本来用。他们就是这样虚假地向诗意的灵感致敬的!就是这样低估评论的价值的!书籍委员会——也有人说是阿根廷文学院——下达了严肃的命令,禁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的范围内对这部我们文学世界中最杰出的注释类作品进行贬低,在此之后,它便获得了一致的认可。然而,损失已经造成;混淆不清的概念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仍有著作家顽固地将拉姆金的分析和佛罗伦萨人的基督教冥世观混为一谈,完全不管它们是如此迥异的作品。也不乏有人被这种类似于摹本的创作体系所带来的复杂蜃景震慑,将拉姆金的作品与巴拉迪翁丰富多彩的多题材写作相提并论。
乌尔巴斯的事例则十分不同。这位如今已颇具声誉的诗人,在一九三八年九月时还很年轻,几乎可以说是默默无闻。依靠不合时宜的出版社举办的文学竞赛卓越评委席上诸位杰出文人的赏识,他才得以脱颖而出。据我们所知,竞赛的主题是玫瑰的古典与永恒。翎笔与钢笔奋笔疾书;大人物的署名时而闪现;当园艺学出现在十四音节诗句或是十音节诗句、八音节三行诗中时,做相关研究的论文里总是一片赞叹,然而,在看似困难却被乌尔巴斯轻松做到的事情面前,这一切都变得黯淡无光,他交上的,是简单却致胜的……一朵玫瑰。没有任何异议;词句——人类所制作的孩子,无法与天然的玫瑰——那上帝的孩子,相媲美。五十万比索最终为这项确凿无疑的壮举加了冕。
广播听众、电视观众,乃至晨报及大量权威医学年刊的执着或偶尔的爱好者都会感到奇怪,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耽搁了如此之久才提到科隆布雷斯事件。不过,我们还是要斗胆暗示一下,事情清楚明了得很,此事件深受各类小报的喜爱,与其说是因为人们赋予它的内在价值,不如说是因为公共卫生系统适时介入时,加斯塔姆彼得医生挥动黄金妙手所做的紧急外科手术。任何人都不敢忘记此次事件,它将会长存于所有人的记忆中。那时(大约在一九四一年)造型艺术馆开始对外开放。人们事先预计,着眼于南极或巴塔哥尼亚的作品将会获得特别奖项。我们不会谈及霍普金斯所奉上的作品,谈及他对冰川或抽象或具象的诠释以及他因此而得到的桂冠,我们要说的是那个巴塔哥尼亚人。这个名叫科隆布雷斯的人,直到当时都十分忠于意大利新理想主义最极端的偏激思想,那一年,他交了一个装钉完好的木箱,当权威们打开它时,从里面跑出了一只健壮的绵羊,它顶伤了不止一位评委会成员的腹股沟,牧羊画家塞萨尔·吉隆虽然依靠山里人的灵活保住了性命,但也被顶伤了后背。这头牲畜可不是假冒的夸张画像,而是一只澳大利亚品种的美利奴朗布耶羊,同时还拥有阿根廷的羊角,这给人们留下了热点地区的印象。这头绵羊就像乌尔巴斯的玫瑰,但它出现的方式更勇猛有力,它并不是艺术的某种精致幻想;而是一个确凿而顽固的生物样本。
出于某种悄悄溜走了的原因,评委会的全体伤残成员拒绝授予科隆布雷斯那个其艺术精神已满怀希望地抚摸过的奖项。“农村”评委会则显得公道、宽容得多,他们毫不犹豫地宣布我们的羊是冠军,自从发生了那件事,它就收获了最棒的那群阿根廷人的热情与喜爱。
由此激发的进退两难的情况着实有趣。如果描述性主义的潮流继续下去,那么艺术将为大自然牺牲自我;不过T.布朗早已说过,大自然就是上帝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