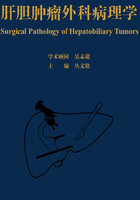
上篇: 导 读 篇 Part Ⅰ Reading Guidence
绪论一 肝癌生物学特性与外科治疗之我见

汤钊猷院士 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
病理是肿瘤外科医生作出决策的前提,我对病理同道的贡献,只有感激之情。 有幸应邀在这本专著的绪论中写一段话,又感到惶恐,毕竟我只是临床医生,不是基础研究人员,好在给我的题目有“我见”二字,为此这段文字,只是从临床角度,讲点个人见解,供同道参考。
2012 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 Engl J Med》刊登了DeVita 和Rosenberg 写的“癌症研究二百年”的文章。 其中1863 年Virchow 关于“癌的细胞起源”,奠定了现代肿瘤学的“病理学基础”,成为癌症诊断的“金标准”和治疗决策的依据;1953 年Watson 等发现去氧核糖核酸(DNA)的双螺旋结构,1979 年发现表皮生长因子(EGF)及其受体(EGFR),1981年发现p53 抑癌基因等,启动了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提示癌症研究的背景已从“病理学”逐步转变为“病理-生物学”。 癌症“病理学基础”的奠定,使抗癌大军的思路集中到一点,即千方百计去消灭病理所证实的肿瘤,这导致外科、放疗、化疗、介入(如经导管动脉内化疗栓塞,TACE)和局部治疗等消灭肿瘤疗法的发展,从而使癌症的疗效有了实质性进步。
作为肿瘤外科医生,体会到从病理学和生物学角度看肝癌有明显不同。 例如:诊断方面,前者重形态,要回答是不是癌,是什么癌;后者重生物学特性,即癌的恶性程度如何。 治疗方面,前者在于消灭肿瘤;后者则旨在降低癌侵袭转移潜能和提高机体抗癌能力。 应用手段方面,前者有手术、放疗、化疗、局部治疗、介入治疗,以及最新的针对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分子靶向治疗剂等;后者则注重生物学相关治疗,如分化诱导治疗、免疫治疗等。 预后指标方面,前者重形态相关的生物学特性,如分化程度;后者则为分子相关的生物学特性,如预后分子预测指标。 疗效评价方面,前者重肿瘤的有效率(完全缓解,部分缓解等),后者重总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鉴于癌症仍远未被攻克,这个背景的转变给临床带来了新的思考,预期癌症治疗未来的趋势,消灭肿瘤仍然是最重要的治疗目标。 但对残余肿瘤的改造,使之恶性程度降低;对机体的改造,以提高其抗癌能力,将成为消灭原发肿瘤后又一重要目标。 这样“改邪归正”或“带瘤生存”便成为治疗的另一“终点(end po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