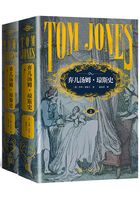
第一章
卷首引言,或筵上菜单。
一个作家,不应自视是以私人身份设宴待客或设食济人的绅士,毋宁自视为开设饭馆的老板,对于所有花钱惠顾的人,一律招揽。在前一种情况下,食物都随招待者之意而定,自不待言,而且即便他之所备,极为草草,使他招待的人难以下咽,而被招待的人,也决不能有所挑剔;不但不能挑剔,他们为礼貌所拘,反倒对于摆在面前的东西,不论是什么,都得虚夸一气,假赞一番。对于开饭馆的老板,情事与此却正相反。凡是光临惠顾的客人,既然掏了腰包,那就不论他们如何食不厌精,如何嗜异成癖,他们也都要坚决要求,给他们端上来的东西,得适口可心;如果不适口可心,那他们就认为,他们有权对所备之物,肆意指摘,尽情诟责,大骂遭瘟该死。
因为有这种情况,所以那班诚实为怀、善良居心的饭馆老板,为了避免因肴馔不合而开罪顾客起见,通常都备有菜单,以便所有光顾的人,一进门来,就可以仔细阅览。顾客通过菜单,对于想要得到的款待,有了清楚的了解,就可以做出决定,或者就在这家饭馆待下来,细细领略给他们预备的东西,或者去到另一家饭馆,享受更可口称心的食物。
对于一切人士,凡是有明达之识或明哲之智 而对二者都不吝赐教的,我们既然都不耻求教,因此对于这般诚实为怀的饭馆老板,我们也移樽请益,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启发;不但对我们全部的款待,先之以菜单总目,并且对本卷和后面各卷所供的每一样飨客之物,还备有菜单分目。
而对二者都不吝赐教的,我们既然都不耻求教,因此对于这般诚实为怀的饭馆老板,我们也移樽请益,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启发;不但对我们全部的款待,先之以菜单总目,并且对本卷和后面各卷所供的每一样飨客之物,还备有菜单分目。
我们这里所备的是什么呢?并非其他,乃是人性。我的读者,既然都通情达理,所以他们尽管最喜珍馐美味,我却从来没担过心,害怕他们会因为我所举出来的肴馔,只有一味,就失惊打怪,吹毛求疵,生气动怒。甲鱼之为物,像布里斯托的区长先生——对肴馔有渊博学识的人——由于见多识广而深知熟悉的那样,除了鳖裙或者鳖边 ,是鲜美的厚味而外,还有许多各样好吃的东西,萃于一身。学识渊博的读者,也不会昧于事理,不知道人性一事,虽然在这儿只概括在一个总的名称之下,却包罗了繁多丰富的品类,所以,尽管世界上有种种荤菜素菜,而一位厨师,却可不用费事,就样样做得出来;但是一个作家,要把人性这个包罗广泛的题材,详尽无遗地精研细究,却非常不易。
,是鲜美的厚味而外,还有许多各样好吃的东西,萃于一身。学识渊博的读者,也不会昧于事理,不知道人性一事,虽然在这儿只概括在一个总的名称之下,却包罗了繁多丰富的品类,所以,尽管世界上有种种荤菜素菜,而一位厨师,却可不用费事,就样样做得出来;但是一个作家,要把人性这个包罗广泛的题材,详尽无遗地精研细究,却非常不易。
令人担心的是:口味更高的人,也许会认为,这盘肴馔太平常、太庸俗,因而提出异议;因为书摊上到处陈列的传记、小说、戏剧、诗歌里面,除了这个题目,不是再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吗?这好像不错;但是,一位专务口腹的人,如果因为在穷乡陋巷中,看到名为甘芳实非甘芳的东西,就据为口实,把所有的甘芳之物,一概以平常、庸俗贬之,那他自然要把许多真正的甘芳之物,当面错过。因为按实在的情况说,在作家所写的东西里,难得看到真正的人性,也正像在铺子里,难得遇到真正的巴庸火腿或者波娄尼亚腊肠 一样。
一样。
不过,如果把这个比喻继续用下去,那就可以说,此书全部的要点,只在作者奏刀的手段;因为,像蒲伯先生告诉我们的那样:
真正的语警识敏,只是自然装点得入化出神,
此亦即心所常忖,而善于表达者永无其人。
同是一头牲畜,身上有的部分,可以享受献于公侯筵上的光荣,而另一些部分,则可以遭到贬抑藐视的耻辱,会像悬于暴尸架上以示众的死囚尸体 一样,挂在市上最令人作呕的肉架上。公侯与隶卒,如果所吃的是同一犍牛或者同一牛犊,那他们所吃的肉,并不会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只能是滋味怎样调和、火候怎样掌握、菜码儿怎样放、杯盘怎样摆这些方面。而也就是由于这些方面,所以,一种肴馔,才能把食欲顶不振、胃口顶不佳的人,都引诱刺激得馋涎欲滴,而另一种,则使食欲最强、胃口最好的人,都大犯恶心,食不下咽。
一样,挂在市上最令人作呕的肉架上。公侯与隶卒,如果所吃的是同一犍牛或者同一牛犊,那他们所吃的肉,并不会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只能是滋味怎样调和、火候怎样掌握、菜码儿怎样放、杯盘怎样摆这些方面。而也就是由于这些方面,所以,一种肴馔,才能把食欲顶不振、胃口顶不佳的人,都引诱刺激得馋涎欲滴,而另一种,则使食欲最强、胃口最好的人,都大犯恶心,食不下咽。
在同样的情况下,怡情悦性之物的优劣,少有赖于选题之当与不当,而多有赖于奏技之巧与不巧。既是这样,那么读者听到后面这番话,一定要非常地高兴:原来我们这个时代,出了一位手艺顶高的厨师,也可以说,连在亥理奥噶巴卢那个时代,也称得起是一位手艺顶高的厨师 ;他有一些高明的原则;我们打算在这部著作里,就谨遵这些原则之中的一条办事。这条原则,像所有讲究精馔美食的人所熟知的那样,就是:宴会开始的时候,客人都饥肠辘辘,他只给以平常的肴馔;随后循序渐进,约计客人的胃口越来越小,品味也跟着越来越高;一直到最后,才把最精最美的浓郁甘芳,端到席上。按照同样的原则,我们刚一开始,要把穷乡僻壤中所看到的平淡朴素一类人性献出,以飨胃口最强的读者,随后才把流行于皇宫王廷和通都大邑那种法兰西和意大利浓烈作料
;他有一些高明的原则;我们打算在这部著作里,就谨遵这些原则之中的一条办事。这条原则,像所有讲究精馔美食的人所熟知的那样,就是:宴会开始的时候,客人都饥肠辘辘,他只给以平常的肴馔;随后循序渐进,约计客人的胃口越来越小,品味也跟着越来越高;一直到最后,才把最精最美的浓郁甘芳,端到席上。按照同样的原则,我们刚一开始,要把穷乡僻壤中所看到的平淡朴素一类人性献出,以飨胃口最强的读者,随后才把流行于皇宫王廷和通都大邑那种法兰西和意大利浓烈作料 ——那也就是,矫性饰情和酒肉声色——全加进去,再快刀精切,文火慢煨。用这种办法,我们相信,就能使读者阅览起来,不忍释卷,像那位伟大名庖能使人饫甘餍肥、猛吞大嚼一样。
——那也就是,矫性饰情和酒肉声色——全加进去,再快刀精切,文火慢煨。用这种办法,我们相信,就能使读者阅览起来,不忍释卷,像那位伟大名庖能使人饫甘餍肥、猛吞大嚼一样。
话既说到这里,那我们现在就不要再使看中了我们这份菜单的诸位,耽搁下去,不得“开吃”了,而直截了当把我们备来请教的头一道醒脾开胃之物献上,以飨嘉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