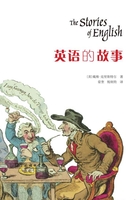
插叙1 凯尔特语之谜
事实上有两个谜。首先,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什么没有最终使用不列颠的凯尔特语?他们到来的时候人数是如此之少,我们或许会希望他们采用本地的语言,因为在一段时间的安居乐业和异族通婚之后,发生这样的事情乃是顺理成章的。比如当时的诺曼底就是如此,那些斯堪的纳维亚入侵者最后都以说法语而告终。英国在1066年以后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诺曼入侵者最后也都说起了英语。但日耳曼入侵者进入不列颠后却保留了他们原来的语言。
第二个谜。当侵略者到达某个国家,并强行推行自己的语言时,他们会吸收当地语言中的词汇,数量往往也都很大。举一个近期的例子,《南非英语词典》(Dictionary of South African English)中就有数以千计的词汇,分别来自南非荷兰语(Afrikaans)、廓萨语(Xhosa)、祖鲁语(Zulu)以及其他一些非洲语言。5虽然英语是作为一种强权语言而到达南非的,但它很快就开始以同化新词的方式反映地区性的事务了。由此我们可以作这样的一般化推理:尽管入侵者以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而告终,但另一种语言依旧会留下自己的存在迹象。维京人于第8世纪后期抵达英格兰,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斯堪的纳维亚语词汇,并曾一度试图影响英语的语法(第76页)。诺曼人接管英格兰时,他们也曾把数千法语词汇带入英语中,最后他们采用了英语,也用法语的拼写惯例(第210页)。那么,在古英语中,为什么很少有凯尔特词汇呢?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周围都是凯尔特语,可为什么他们却没有受到影响呢?
除第25页提到的地名之外,影响确实很小,许多被用作实例的单词,从词源学角度看,其所谓的凯尔特词源都是值得怀疑的。一个单词到底是不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到来之后从威尔士语进入古英语的,抑或是尚在大陆的时候就已经从拉丁语进入了,因而在盎格鲁-撒克逊语中早已存在?要想说清类似的问题,有时是非常困难的。比如bin[容器]既可能源自早期不列颠语的benna(比较威尔士语的ben“马车”),也可能源自早期拉丁语的benna。Assen[驴]大概来自古不列颠语的assen,但也可能更早,来自拉丁语的asinus。还有一些情况,部分单词有可能出自凯尔特语,但是由于在日耳曼语支的一些语言中有着对等的形式,所以这一点并不肯定。比如puck[恶魔](威尔士语pwca),在古挪威语中就有一个近似的形式puki;再如crock“壶”也可以在好几种斯堪的纳维亚语中找到,比如冰岛语的krukka。
古英语词汇中,看上去确实与凯尔特语有明显关系的词语包括bannoc[面包、糕点],broc[獾],cammoc(即cammock,一种植物),crag(“峭壁”,比较威尔士语的craig或carreg),dunn(“棕绿色”,比较威尔士语的dwn)和wan(“暗”,比较威尔士语的gwan)。具体到wan,虽在日耳曼语中不见其踪影,但在《贝奥武甫》(第702行)中却有出现:Com on wanre niht scithan sceadugenga。这句话在约翰·克拉克·霍尔(John Clark Hall)的英译中是The creature of the shadows came stalking in the dusky night[这黑暗的造物在朦胧的夜色中潜伏而来]。 另有三个凯尔特词汇出现在诺森伯兰语的文本中,显示出不列颠人正向遥远的北方挺进,这三个词是bratt[斗篷],carr[岩石]和luh[湖泊]。我们还必须在这份清单中加入几个由爱尔兰传教士引入的单词,比如anchorite[隐士],clucge[响铃]和dry(“男巫”,比较druid[德鲁伊特教徒])。《牛津英语词典》列举了几个单词,自身词源不明,可能与凯尔特语有联系,但是即便我们将它们全部包括进来,也无非是给我们的讨论增加20个左右的后备例词而已。另有一定数量的凯尔特语词汇的确进入英语之中,比如brogue[皮鞋]、coracle[小圆舟]和plaid[格子呢],但那都是古英语形成之后很久的事了。
解释虽然各种各样,但也都只是猜测而已。也许凯尔特人的生活方式是在罗马的不列颠形成的,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生活方式则是在欧洲大陆形成的,二者之间根本就很少有什么共同之处,所以也不存在任何理由去借用凯尔特词汇。相反,或许还存在一种明显的回避意识。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发生,如果盎格鲁-撒克逊人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高于那些“野蛮人”,他们就会将凯尔特词汇看作“粗鄙的语言”(gutter-speak)。或许他们之所以回避,还有一个完全相反的理由:因为很多凯尔特人都可能被高度罗马化了(罗马人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已有400年的历史),或许他们已经把自己看成了“暴发户”(neuveau riche),所以希望远离那种所谓的“上等人的”(posh)腔调。由于时间不同,地点不同,这两种因素都是能够成立的。
此外,还可能涉及一条截然不同的思路。或许两种生活方式都极其相似,所以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拥有了他们所需的全部词汇。盎格鲁-撒克逊人所接受的凯尔特词汇,应该是他们认为的最有用的部分,很可能早已经由拉丁语而进到了他们的语言,因为罗马人本身就在欧洲。从他们在大陆与罗马人的接触当中,他们至少应该熟悉许多拉丁单词。从这一点看,拉丁语——作为一种承载政治权力的语言——也一定是词汇的来源,其吸引力还可能大于威尔士语。对此,爱尔兰传教士的故事也许是一个佐证。他们来到不列颠时,就曾将拉丁语作为一种不同的力量来看待。凯尔特人也一样,很可能熟悉拉丁语;在罗马-凯尔特时代(Romano-Celtic years),一定有很多会讲拉丁语的凯尔特人。拉丁语必然影响早期凯尔特语,这可以从某些词形中得到证明,比如威尔士词汇eglwys(“教堂”,源自ecclesia),又如ysgol(“学校”,源自schola)等。这样的影响还见于几个早期地名之中,因为不少地方的名字,其英语形式都源自ecclesia,比如Eccles,Eccleshall,Eccleston(见嵌板1.6)。

基因检测的结果正在提供一种新的证据,我们可借以理解这样的情况。根据2002年的一份研究报告,6在东英吉利亚至北威尔士的东北一带,人们对七个城镇作了截面的抽样研究,结果显示,男人之间的Y-染色体有着显著区别,表明大批凯尔特人曾经进入英格兰,而在英格兰的当地凯尔特人中,至少一半的男性曾被他人取代。研究人员还在英吉利男子和弗里斯兰男子之间识别出惊人的基因相似性,所以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威尔士边界俨然是个基因屏障(genetic barrier),比北海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此重大的人口迁徙运动,让人联想起我们今天所说的“种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其恶果之一便是对凯尔特人的憎恨,包括他们的一切,尤其是他们的语言。任何人都不会从他们的驱逐对象那里借用词语的。
但是,从人名而来的语言学证据,却并不完全支持这样的故事。盎格鲁-撒克逊的望族很少使用凯尔特的姓氏。即便偶尔使用,也都往往彰显着别样的情趣。Cadwalla[卡德瓦剌]、Ceadda[查达]、Cedd[彻德]、Ceawlin[查林]和Cumbra[昆布拉]都是威尔士人的姓氏。比如Cumbra就非常近似于威尔士的Cymro(“威尔士人”)。有趣的是,所有这些姓氏都属于盎格鲁-撒克逊的贵族成员。比如Cadwalla,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记载,他曾是韦塞克斯的国王(685年),比得(第5卷第7章)也曾叙述过他皈依基督教的故事。但Cœdwalla这个姓显然来自威尔士语。事实上,另外还有一个与他同姓的人,即威尔士国王圭内斯的卡德瓦拉(Cadwalla of Gwynedd)——比得(第2卷第20章)称他是“不列顿之王”(king of Briton)——他曾于633年杀死了诺森伯兰国王埃德温(Edwin)。盎格鲁-撒克逊王室居然采用威尔士人的名字,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
但凡做父母的人都知道,对于如何选择名字,人们也都是极其敏感的。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往往会花费很大心思。在给自己的孩子取名时,没有人会用敌人的名字,或那些让人感到脸上无光的人的名字。处于战争状态时,人们甚至会更改自己的名字,以避免遭人误解。著名的例子是1917年的英国王室,当时的乔治五世就将Saxe-Coburg-Gotha[撒克斯-科堡-哥达]更名为Windsor[温莎]。另一方面,选择自己由衷爱戴或心怀感激的人,取他们的名字为孩子的名字,却又是一种常见的做法——不论这个人是否是老一辈的亲戚或家族的朋友,也不论是否是业务伙伴或政治盟友。同时人们也受社会风气的深刻影响:有的名字会十分流行,现代的报刊还登载些年度名册,刊出最为时髦的名字供人选择。宗教也有很强的影响力,比如那些圣徒或圣经人物的名字。在古代——一如今天的很多社会一样——名字的意义往往被赋予极高的期待,所以孩子的名字通常会有特别的所指,比如“有福的”、“像基督一样的”等等。
所以,如果某些盎格鲁-撒克逊贵族在为他们的孩子取名时,用了不列颠人的名字,这本身至少意味着,他们对凯尔特社会中的某些成员十分尊敬,而那个社会就在不列颠的某些历史阶段。一个合理的解释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族长与罗马-凯尔特的贵族成员,双方共同生活,非常融洽,并互通婚配。孩子的名字既可取自甲方家族的某个长者,也可取自乙方家族的某个长者,这就很容易用上凯尔特人的名字,就像用日耳曼人的名字一样。这些孩子中,有些也将成为贵族,而名字的使用会有助于事理的传播。如果家庭中的长辈这样做了,那么晚辈也会把它当作时髦,并如法炮制。我们无从知道是谁生养了凯德蒙(Cædmon)——这个第7世纪的僧院马夫,根据比得的记载(第4卷第24章),后来成了英格兰的第一位基督教诗人——但他的父母给了他一个威尔士人的名字。这种与凯尔特传统的亲密接触,其结果竟然没能让更多的凯尔特单词汇入到古英语之中,其中究竟有着怎样的缘由,迄今为止依然是语言史上的一大谜团。
1 此译文摘自Everyman Library edition(Bede, 1910),原为18世纪J. Stevens的译文,后曾经过校订。
2 见Blair(1977: 10-11)。
3 基因研究报告见Weale, Weiss, Jager, Bradman, and Thomas(2002)。
4 要进一步了解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及其史前史,请参阅Blair(1977)和Patridge(1982)。历史与考古的图片资料及其文字说明与翻译,见Mitchell(1995)。有关方言溯源的讨论,见DeCamp(1958)和Toon(1992)。
5 关于南非英语,见Branford and Branford (1991)。
6 见Weale, et al.(2002)。